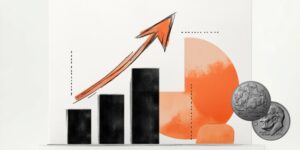图片源于:https://www.lowyinstitute.org/the-interpreter/lessons-australia-s-policy-dilemmas-america-s-post-neoliberal-delusion
在《外交事务》最新一期的一篇文章中,哈佛大学经济政策教授、白宫经济顾问委员会前主席杰森·福尔曼对”拜登经济学”—一种后新自由主义政策的尝试,进行了批评。
这一政策试图以热火朝天的方式推动经济运行,并采取积极的产业政策。
澳大利亚并不具备美联储货币的金融优势,也没有像美国那样庞大而多样化的经济,但仍可借鉴拜登政府试图替代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的方法。
福尔曼的批评是一个良好的开端。
新自由主义经济方法存在两个主要批评点——不平等和外部性。
拜登的异端政策未能解决这两个批评点。
允许市场在相对自由的环境中运作,包括相对自由的贸易,必然会产生赢家与输家。
问题在于,尽管赢家可以补偿输家,但这并没有保证。
输家可能在地理上或其他方面集中,例如在锈带州,以及那些没有大学学历的制造业工人。
市场无视了因失去工作和投资所带来的直接成本和间接成本。
这些间接成本可能相当可观,范围包括阿片类药物流行病到由于收入和财富在高储蓄家庭中越来越集中而导致的长期停滞。
福尔曼指出,美国政府传统上通过扩大社会安全网和/或中产阶级福利来减少这些间接成本。
然而,尽管拜登向家庭提供了刺激支票,但并未将扩大的儿童税收抵免纳入长期政策,或提高最低工资,这将为市场驱动的不平等提供更持久的对抗力量。
随着政治家回应利益集团提出的担忧,监管迅速扩大。
虽然许多担忧是合理的,但过多的监管失去了内化外部性的目标——迫使做出关于生产、消费或行为的决策者考虑并为对他人和未来的伤害付出代价。
经济学家更偏好定价方式,但通过监管要求限制选择则更为普遍。
即便能够征收价格(或罚款),监管体系往往变得繁琐,行政成本高昂,决策速度缓慢。
尽管上诉权可以改善公平性,但它也增加了成本,并可能成为拖延决策的机制。
福尔曼正确地批评了拜登的基础设施投资政策,指出其未能解决导致美国主要基础设施项目财政和时间成本上升的监管障碍。
福尔曼还批评拜登经济团队未能认识到其后新自由主义”异端”政策解决方案的固有经济Constraints。
福尔曼列出了未能认识到预算约束、成本收益分析和权衡,这也是“拜登经济学”未能实现承诺的原因之一:实际工资的上升、制造业就业的增加和基础设施建设的繁荣。
福尔曼提到,赤字支出的上升对利率造成了影响,但应当承认,美国有着令人羡慕的能力,可以以远低于其他国家的成本融资不断增长的政府债务。
正如丽兹·特拉斯在英国所发现的,财务市场对绝大多数政府在财政上不理智的政策反应更为迅速。
但即便是美国也不能免于宏观经济约束,因为刺激支付、积压的延迟需求、记录家庭储蓄、供应链限制以及政府投资计划的结合,推动了更高、更长时间的通货膨胀。
随着政府项目与工人和材料的竞争,私人部门的投资被挤出。
在预算约束存在的情况下,政府活动必然会挤出私人活动。
福尔曼的批评隐含着预算约束适用于劳动力和可用技能,正如同适用于政府预算。
当需求上升碰到预算约束时,价格会上涨。
处于需求中的工人和行业(包括外国出口商)是赢家,但其他人在成本上涨速度超过工资或价格时则成为输家。
福尔曼对拜登的产业政策提出了相同的批评。
他承认,”芯片法案”等政策可能出于国家安全目标,旨在将计算机芯片制造业带回美国。
但他对拜登的“本地化”政策持更为批评的态度,例如政府采购的“买美国货”规则、保留特朗普的关税、限制绿色技术的进口,以及《通货膨胀削减法案》中的绿色技术的巨额补贴和税收优惠。
这些产业政策尚未带来更多的制造业工作,部分原因在于建立新工厂需要时间,但制造业也在持续实现自动化。
福尔曼指出,针对特定行业的政策并不能解决赢家和输家的问题,它只是改变了这些群体。
有权衡存在,与通过市场定价碳排放来解决问题相比,《通货膨胀削减法案》不仅成本更高,而且在减少排放方面的时效性也更差。
正如我们常常从失败中学到比成功更多的教训,澳大利亚可以从拜登经济学中吸取诸多教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