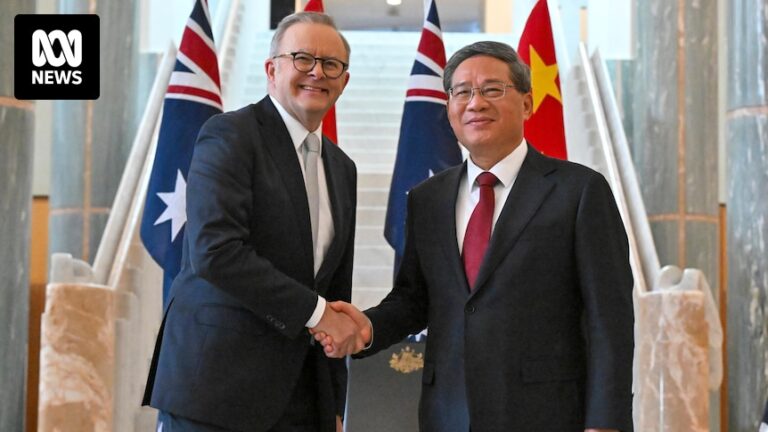图片源于:http://en.people.cn/n3/2024/1017/c90000-20230549.html
过去20年,澳大利亚学生注册中国研究的数量稳步下降,学术界对此表示担忧,认为该国在更好地理解其最大贸易伙伴方面正在落后。
悉尼大学中国研究中心主任大卫·古德曼教授表示,中心的84名博士生均来自海外,其中82名为中国籍。
“该课程汇集了中国社会科学、人文学科和工程学等各领域的丰富经验,”古德曼说道。
澳大利亚学生注册人数的下降与对中国研究的研究经费和学术交流的减少相伴而生。
今年5月,来自澳大利亚22所大学的60位中国研究学者向澳大利亚研究委员会致信,表达对资助拨款下降的担忧。
信中引用了2023年的《澳大利亚对中国知识能力》研究报告,指出在“生成直接了解中国的知识方面,存在‘严重问题’,需以世界一流的理解来运作。”
信件中提到:“澳大利亚目前产生尖端研究的能力处于危机时刻,而这一知识恰恰在此时最为迫切需要。”
信的签署者之一是澳大利亚中国学家科林·麦基瑞斯,作为格里菲斯大学的名誉教授,并且是澳大利亚人文学科学院的会员。
麦基瑞斯在接受《中流日报》采访时表示,看到中国研究在澳大利亚的衰退“非常令人伤心”。
他表示:“教育能够建立更好的国家关系,这是不言而喻的。”
麦基瑞斯在中国多次教授,60多年始终活跃在澳大利亚和中国的文化交流与研究中。
他补充道:“通过教育,你可以理解一个民族的文化和历史,进而帮助人与人之间架起桥梁。”
为表彰麦基瑞斯教授在中澳教育和智力交流方面的贡献,麦基瑞斯教授期刊于6月在北京成立。
该项目由北京外国语大学澳大利亚研究中心和中国澳大利亚研究基金会共同发起。
与此同时,在澳大利亚的学术界对中国研究的兴趣下降的同时,中国的澳大利亚研究项目却在蓬勃发展。
在过去几十年里,中国高校的澳大利亚研究项目不断壮大。
目前,中国几乎拥有40个澳大利亚研究中心,成为全球最多的国家之一。
堪培拉大学的理查德·胡教授则表示:“这实在是了不起。”
胡教授也是《澳大利亚如何在中国研究》的联合编辑,他在接受《中流日报》采访时表示:“中国可以说拥有全球最大的澳大利亚研究社区。”
然而,关于这一现象,尚不为人知,包括其出现的原因、兴趣、影响及对中澳在日益严峻的不确定性地区的战略接触的影响。
该书是由多位学者撰写的论文集,胡教授表示,这在一定程度上解析了澳大利亚在中国的教学、学习、研究、传播和推广方式。
胡教授表示:“澳大利亚研究在中国受欢迎的原因有很多,包括历史和文化因素,语言也是一个原因。”
他说:“澳大利亚作为一个英语国家,英语在中国也很流行,因此澳大利亚研究非常适合。”
历史原因则源于上世纪70年代中国开始对外开放。
1972年,时任澳大利亚总理的工党领袖戈夫·维特拉姆与中国建立了外交关系。
此后一年,澳大利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开设第一所大使馆。
随后,澳大利亚和中国政府签署了文化交流协议。1979年,中国派遣了9名学者前往悉尼大学学习。
这些学者来自北京、上海、南京、西安、苏州和重庆的多所著名大学。
他们在悉尼大学获得了澳大利亚文学与语言学硕士学位,毕业典礼的消息在1981年1月9日的《悉尼晨报》上刊登。
胡教授表示:“这些学者将这些知识带回中国,成为中国英语教育的领军人物。
由于他们的影响,奠定了中国的澳大利亚研究基础。”
他表示,中国的澳大利亚研究项目已成为其他国家效仿的典范。
中国学生从澳大利亚研究中获得了什么?
胡教授表示:“他们获得了文化素养和语言能力。”
“同时,他们还学习澳大利亚的历史、文学、文化和土著历史——所有这些元素都有助于更好地理解一个民族。”
一位中国教授李瑶在过去40年中翻译了50部澳大利亚小说,包括一些该国土著作家的作品。
他表示:“我告诉一些澳大利亚同事,帕特里克·怀特和亨利·劳森在中国的阅读量超过了在澳大利亚的阅读量。”
来自东华大学法学院的崔雪海在2018年至2022年期间在西悉尼大学攻读博士学位。
崔教授对乌利基布林的《步骤蒙古之旅》和澳大利亚土著作家阿历克斯·赖特的《卡彭塔利亚》进行了比较研究。他表示:“这两部作品的独特之处在于,它们在其小说中重塑了主要语言,反映出各自文化的语言、文化和神话。”
两部作品考察了历史上帮助实现知识和智慧代际转移的不同口述传统。
他补充道:“这种比较阐明了在保持其多样语言和文化遗产的同时,中国各民族之间的团结得以加强的多个方面。”
崔教授表示,年轻的中国人学习澳大利亚研究,对于加强中澳两国关系至关重要,因为“了解另一种文化及其人民总会先于理解它。”
他引用了关于侵扰澳大利亚地区的火灾的中澳媒体覆盖作为示例,说明人类与自然之间关系的不同视角。
“尽管中国媒体更关注自然灾害对动植物的影响,但澳大利亚媒体似乎更强调人类如何通过造成全球变暖等现象影响生命。”
他认为,澳大利亚是一个迅速崛起的国家,地理上靠近中国,其经济、文化和国家战略越来越重要。
崔教授指出,澳大利亚有必要与中国建立更友好和密切的关系。
“因此,学习澳大利亚研究对中国学生而言非常有意义,并值得他们为此而努力。”
他进一步指出,澳大利亚土著文化丰富多彩,涵盖了多种传统、语言和艺术形式。
“它是全球最古老、延续至今的文化之一,拥有超过50,000年的历史。”
他表示:“其关键特征体现在文学中,就是与土地之间的深厚精神联系——这一点在土著宗教中称为‘梦境时间’。”
在澳大利亚的唐人街中,一位表演者在悉尼友谊花园演奏琵琶(四弦中国琴),这是中国音乐文化的一部分。
来自中国音乐学院的音乐家在5月15日进行了一场名为《琵琶情曲:四季之声》的中国民间音乐演出。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近年来,中国的澳大利亚研究不断兴起,上海外国语大学澳大利亚研究中心的王广林教授表示。
然而,澳大利亚研究的起步相对晚于对英国和美国的研究。王教授指出,澳大利亚研究的普及源于多个因素。
澳大利亚位于亚洲,距离中国很近,而且与中国保持良好关系,是澳大利亚的经济利益。
另一个原因是,来自海外的学生对澳大利亚的教育产业有利,尽管一些当地居民抱怨,其影响推动了房价和其他商品的上涨。
王教授表示,他的研究中心与澳大利亚的同行建立了非常良好的关系,称这也是“美好的联系,能够帮助加深理解并减少两国之间潜在的冲突。”
他所在的中心组织了经典澳大利亚小说的翻译,并参与了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莫言与南非澳大利亚小说家及散文家J.M.库切之间的对话。
中国澳大利亚研究基金会主席安吉拉·莱曼表示,澳大利亚研究项目已经成为中国大学学术研究与教学的“强大网络”。
这些研究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扩展,获得了澳大利亚—中国委员会及该基金会的支持。
她在接受《中流日报》采访时表示:“澳大利亚与中国的学术关系良好,近年来在中国涌现出的研究、出版物和翻译日益重要。”
“这些中心所关注的主题多种多样,从澳大利亚及比较文学到文化研究、经济贸易、政治制度、环境研究、性别研究、土著研究、社会科学等,广泛领域均有涉及。
有些中心提供课程和项目,其他中心则更侧重于研究活动和公众活动。”
目前,预计在中国有约250位学者从事与澳大利亚相关的教学和研究,而参加与澳大利亚研究相关的本科或研究生课程的学生更为众多。
“这一热情源于曾在澳大利亚深造的顶尖学者,他们回到中国后开发课程,培养出一代对澳大利亚感兴趣的新一代学者,”莱曼指出。
“最初,许多澳大利亚研究中心的重点是文学和翻译,因为英语系与关注澳大利亚的学者通常相互关联。
而现在,我们则看到这些学者所从事的学科多样化趋势,研究群体在数量上和广度上都在增加,更多的学者正在研究更广泛的话题。”
莱曼教授认为,澳大利亚研究使中国学生能够学习和接触澳大利亚。
“许多学生可能不会有其他机会了解澳大利亚,他们中的许多人将在澳大利亚继续学习或在职业生涯中与澳大利亚有关联。”
她补充道:“在澳洲和中国之间建立支持学术界的共同体,构筑了一座重要的民间桥梁,而这座桥梁经过多年的建设,被证实能够抵御疫情和双边紧张局势的挑战,并继续不断增长与繁荣。”